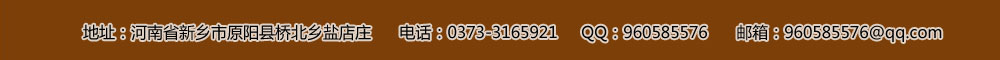爱和生命的延续
医院。那天,在ICU门口的服务台上看到立着的一块牌子,电脑屏幕大小,上面写着“XX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咨询处”。器官捐献这件事其实并不陌生,但第一次感觉这件事离自己那么近,不在别人的讲述中,也不在新闻报道中。就在眼前,那么真实。我取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,存起来,好像在未来的某一天,上面的电话号码自己会用上似的。器官捐献,在人们心里一直是一件严肃,切不寻常的事。捐献者、医生、受捐者,他们之间有一条神奇的纽带,联结着不同的人,完成生命的延续。W是医生,经常讲一些真实的故事给我听。
有一位老人,三月的时候,在内蒙古赤峰因病逝世。根据遗愿,她逝世后由家属配合,将一双眼角膜分别捐献给赤峰和天津。老人年从天津师范大学毕业后,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,在内蒙古林学院和赤峰卫校教学35年,为当地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,桃李满天下。
她捐献角膜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。她生前这样说,“我在天津出生,上学,那是我的故乡,我要把一只角膜捐给天津人民;我在内蒙古赤峰工作了一辈子,要把另一只角膜捐给赤峰人民。让更多人看到光明,我呢,还能看到小康社会。无怨无悔的,诚心诚意的,为残疾人解除他们的黑暗。”这番朴实的话,句句真诚而有力,像一道光,照亮了人心。之后,医院、红十字会、医院,多方配合。经过摘取、保存、运输、交接、手术等环节,顺利护送老人的眼角膜回到故乡,帮助老人完成了她的心愿。运往天津的一只角膜,让一位因右眼角膜白斑失明5年的残疾人重见光明。
像这样的异地器官捐献,工作相对复杂。为确保器官的活性,必须摘取及时,保存得当,器官交接和受捐者手术,各环节的对接需要畅通及时。正因为时间的紧迫,也会发生一些让人尴尬的场面,确切地说,心疼多于尴尬。
W说,一次他们接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摘取的任务。有两位患者,自愿捐献眼角膜,当地红十字会帮助协调三方——捐献者、医院医院。为确保在捐献者死亡的第一时间完成器官摘取,受委托的医生要随时待命。一天,他们接到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通知,医院。当他们提着手术箱来到捐献者面前时,二人就坐在病床上,其中一个还是个孩子。他们睁着眼睛,看着赶来的两位陌生医生。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这两位医生是专程来摘取他们器官的,也或许他们想到了。总之,医生定在了门口。协调员尴尬地说:“抢救成功,生命很顽强。”的确很尴尬,他说,医生明明是应该冲在挽救生命的第一线,可那一刻看起来,却活像是在等待和盼着患者的死亡似的。第一次觉得自己以这样的方式站在病人面前,那么不合时宜,心中五味杂陈。
几天后,他们再一次接到通知前往。
因为角膜的捐献需要摘取整只眼睛,手术结束的当天,他们提着装有四只眼睛的储存箱,医院进行移植交接。那眼睛,正是前几日他们相互凝望过的眼睛。医者仁心,他们的工作职责更多是为了生的人,但医生也是普通人,对死者同样也怀有人性的尊重和悲悯。无论是捐献者、医生,还是受捐者,他们都在参与着一种充满爱的行动。这爱,是明亮的眼睛,是跳动的心脏,亦或是清澈的呼吸;这爱是生命的延续,是能量在流动,是世间的慈悲。
“器官捐献,生命永续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。”
—end—
作者简介
斯琴
有为,不执于业果,结果,轮回中的一点经过。
_siqin
回复关键词:“斯琴”,阅读斯琴往期作品